|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10-08 02:26:04 发表 |
穆勒枢机谈教宗的牧职方向,以及教廷与LGBTQ+争议…
意欧视点
日前,圣座教义部荣休部长格尔哈德·路德维希·穆勒枢机(Gerhard Ludwig Müller)就教宗良十四世执政初期的若干议题发表了看法。穆勒枢机的论述立足于天主教教义与神学传统,为理解当前圣座的牧灵方向提供了重要视角。
穆勒枢机首先肯定了教宗良十四世在牧职开端所展现的“以基督为中心”(cristocentrismo)的取向。他指出,这种“基督中心”的态度是必要的,因为教会的首要使命并非政治或社会倡议,而是“向众人宣讲得救的福音与永生”。他表示,虽然社会和政治议题在教会的社会训导中占有地位,但它们永远不能取代信仰的核心使命。
在谈及教会治理的主教集体性原则(collegialità episcopale)时,穆勒枢机指出,主教共治并非行政手段,而是信仰与教义的内在组成部分。教宗作为罗马主教,并非孤立的权威,而是与枢机团(collegio dei cardinali)协同行使牧职。枢机们的职责,是在智识与道德层面上协助教宗,为教会合一与信仰生活提供支持。
针对部分舆论将教宗良称为“回归传统”的象征,穆勒枢机认为,这种标签化解读是不恰当的。他以教宗佩戴肩衣(mozzetta)为例,解释这是职务的象征,而非个人风格的展示。教宗良的意向,是更清晰地体现伯多禄继任者(successore di Pietro)的角色,而非以个人魅力塑造形象。
关于拉丁礼弥撒(messa in latino)的问题,穆勒枢机指出,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并未改变弥撒的本质,只是调整了部分礼仪形式,以促进信友更积极地参与礼仪生活。他承认部分信友对1962年后的礼仪形式仍存保留,这些“传统主义者”(tradizionalisti)表达了他们的感情与信仰敏感度,但强调“不能认为唯有旧式拉丁弥撒才有效”。他认为,应区分圣事的本质与礼仪形式的可变性,寻求一种基于天主教思想的包容与协调,而非依靠权威命令来解决。
针对近期关于“LGBTQ+群体禧年”(giubileo della comunità Lgbtq+)的争论,穆勒枢机作出了明确回应。他指出:“圣年(Anno Santo)与圣门(Porta Santa)不能被意识形态化或政治化。”他强调,教会奉基督之名接纳所有人及他们的处境,但必须忠于信仰教义:“上帝创造男与女,这样的婚姻是唯一可以以夫妻方式共度生活(vivere coniugalmente)的可能。”
穆勒枢机指出,圣门象征的是进入基督、进入天主家庭的道路,而非特定群体政治诉求的标志。基督徒的召叫,是克服敌意,而不是击败敌人。
谈到教宗多次重申的“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Todos, todos, todos/Tutti, tutti, tutti)的牧灵原则时,穆勒枢机解释说,所有人都被召唤去寻求耶稣基督,但这同时意味着生命的改变与皈依。他指出,有人误解“所有人”是指无条件接纳一切生活方式,这并不符合福音精神。为说明这一点,他举例说,早期教会时期的角斗士(gladiatori)在受洗前必须放弃其暴力职业,显示信仰始终要求个人生活的更新与转化。
对于教宗关于堕胎、死刑及移民的相关报道,穆勒枢机也作出澄清。他表示,教宗并非意图把这些问题“相对化”,而是要求信徒在维护生命尊严的各个层面保持主体一致性(coerenza soggettiva)。他重申:“堕胎是杀害无辜者的行为,是残忍的罪行。”但这不能与针对杀人罪犯的死刑等同。他个人反对死刑,但指出教会在历史上,在极端限制情况下,曾承认民事当局的惩罚权。关于移民议题,他主张信徒应以弟兄般的爱接纳他人,同时承认各国政府有责任规范非法移民,保护本国公民免受可能的犯罪威胁。
在谈及对教宗牧职的期待时,穆勒枢机期望“看到关乎天主圣言的惊喜,而非世俗意义上的轰动”。他强调,教宗不是公众人物或媒体偶像,不应按照好莱坞式的规则塑造形象,而应如善牧一般,为基督的羊群献出生命。总而言之,穆勒枢机认为,教会的中心永远是基督,而非个人或意识形态。
据介绍,穆勒枢机于1947年出生于德国,是当代天主教会内一位极具分量的神学家和高级神职人员。他因其在神学上坚定的正统立场以及对天主教教义严谨而不妥协的捍卫,被广泛视为教会内保守派(在教会语境中更常被称为“正统派”或“信理捍卫者”)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长期从事神学学术研究,曾是德国著名的天主教神学教授,在系统神学与教义史领域著述颇丰。他尤其因其与梵蒂冈信理部前部长、后来的教宗本笃十六世在神学上的密切关联而备受关注。穆勒曾主持编辑《本笃十六世作品集》的出版工作,二人亦合著过关于神学的书籍,这体现了他们在神学思想上的高度一致性。
2012年,教宗本笃十六世任命他为圣座教义部部长,并擢升为枢机。圣座教义部是罗马教廷中最为重要的部会之一,负责维护信仰与道德的纯洁性、正统性,其职责范围包括审查神学著作、处理重大信理问题等。2017年穆勒枢机卸任,成为圣座教义部荣休部长。总而言之,穆勒枢机是一位学者型枢机。他代表了天主教会内一种强调传承、教义清晰和神学严谨的声音。理解他的观点,对于全面把握当代天主教会内部关于现代性、传统与革新之间复杂而持续的对话与张力,至关重要。
——
看完这篇文章,中国天主教那些自以为是的保守派心凉了半截,呵呵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10-01 08:15:02 发表 |
习近平:推动宗教严格执法 引导教义礼仪体现中国特色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一(9月29日)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总结运用历史经验,加强体制规范建设、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系统推进在华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习近平并要求推动宗教严格执法,引导教义礼仪体现中国特色。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一下午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聚焦系统推进在华宗教中国化。中央统战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张训谋就该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讲话,指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把宗教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鲜明提出坚持在华宗教中国化方向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完善宗教工作体制机制,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推动宗教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习近平表示,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不断推进在华宗教中国化,才能促进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由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必然要求。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并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五个认同”指的是对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习近平指出,中国各宗教只有始终扎根中华大地、浸润中华文化,才能健康传承。要植根中华五千年文明,推动在华宗教同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感。
习近平强调,激发宗教界主动作为、自我变革,对推进在华宗教中国化至关重要。要支持引导宗教界在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礼仪习俗、行为规范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适应时代要求,提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水平。
中国古刹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今年7月底官宣被查。官方通报指他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和寺院资产,还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
习近平指出,依法治理宗教事务,是正确处理宗教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完善相关法规和政策,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动严格执法,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习近平强调,各级中共党委要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中共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深化战略性、基础性、现实性问题研究,加强宗教工作队伍建设,夯实基层基础,进一步形成推进在华宗教中国化的合力。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9-18 06:13:07 发表 |
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研究员、前助理国防部长帮办施灿德(Chad Sbragia),星期三(9月17日)在北京香山论坛对话上说,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上周有关“不寻求与中国冲突”的说法,标志着美国政策出现“重大转变”,特朗普政府正寻求与中国“共存”之道。
施灿德在场边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强调,眼下唯一重要的是:中美不要开战,否则世界不复存在。
与施灿德同台的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则回应,如果美国能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将极有利于中美实现和平共存。
北京香山论坛星期三至星期五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星期四举行开幕式。
在中美刚结束马德里回合经贸谈判、两国领导人即将通话大背景下, 施灿德与吴心伯围绕“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主题展开对话,座无虚席。
在主持人提问后,施灿德发言时首先指出,赫格塞斯上周与中国防长董军通话时提出,“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也不寻求中国政权更迭或扼杀中国”的说法,“独特且史无前例”。他认为,这“标志着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特朗普政府正寻求与中国共存之道。
——
但亚洲新闻仍在寻求“推翻共产党”,反华人士只有郁郁而终这个结局。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9-15 05:03:59 发表 |
| 今后的教宗都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你们慢慢抵制,呵呵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9-15 05:01:09 发表 |
| 天主教这些反华媒体以前说方济各“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现在是不是继续说良十四“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呵呵!宗教媒体甘做美国的政治工具,你们算老几?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9-15 04:51:59 发表 |
| 为什么陈日君强烈抵制“同道协行”?因为同道协行让平信徒有投票权,而中国爱国会的民主办教也是让平信徒有投票权(即使是形式上走个流程)。但是,你们抵制又怎么样?良十四支持。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9-09 17:28:51 发表 |
鼓吹末世论裹挟未成年人 山东小学教师等发展一贯道落网
中国近年加强宗教管理,严厉打击邪教。山东安丘警方破获一起一贯道复辟案,以末世论精神控制信众,有逾600人,包括30多名未成年人被裹挟,目前三名主犯已判刑。
据中国反邪教网星期一(9月8日)发布的消息,去年4月以来,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公安侦破一起一贯道复辟案件。
经查,该组织利用会道门(民间秘密结社组织,以宗教异端信仰为特征)歪理邪说蛊惑、诈骗群众,2022年至2024年初迅速裹挟成员600余人,其中未成年人达30余人。
该组织被指鼓吹“发展成员年龄越小,功德越大”,严重扭曲未成年人价值观,危害社会安全稳定。
通报称,一贯道信奉“无生老母”,宣扬“(儒、释、道、基督、回)五教同源”“五教合一”“三期末劫”,宣称当下为“末法时代”(“世界末日”),只有加入组织方可“得到救赎、不再受轮回之苦”等邪说。该组织并通过要求成员缴纳“功德费”、出售书籍等方式敛财。
公安发现,涉案刘姓主嫌为小学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诱骗20余名在校学生加入,以个人收入作为“功德费”,每日花六至七小时从事修行活动,严重影响工作与家庭生活。
调查发现,一名董姓女子的案例显示,因她遭遇家庭困境、疾病折磨及亲情缺失等困境,被“邪说蛊惑”,由普通成员逐步成为“佛坛坛主”,不仅延误治疗,也对家庭造成更大影响。
警方表示,该组织利用人生低谷的心理弱点,宣称“三宝”可“逆天改命”,吸引受害者。
通报指,涉案组织架构严密,设有“点传师、坛主、普通成员”多层级,活动范围达山东省内九个地级市,并辐射全中国大陆。该组织还通过熟人网络发展成员,要求参加实体聚会、线上课程,并授予职务、分配任务,逐步把成员纳入组织运作体系,限制与社会的正常联系。
涉案刘姓、苑姓、董姓等主犯,已被中国官方处以拘役六个月至三年不等,罚金6000至2万元人民币(1079至3600新元)不等。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9-05 02:14:45 发表 |
香港主教:教宗认同教会与北京对话重要性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与教宗良十四世就中国教会交流意见后指出,教宗认同教会与中国政府对话的重要性。
据天主教香港教区《公教报》报道,周守仁星期二(9月2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与良十四世会面,这是周守仁今年5月在梵蒂冈参与选举教宗会议、祝贺新当选的教宗良十四世后,两人首次深入会面。
周守仁称,这次会面让两人互相加深了认识,他跟良十四世分享了自己对教会的看法,以及有关在中国教会和香港教会的情况,帮助良十四世加深了解中梵关系的现况。
周守仁还说,相信良十四世持续了解中国教会的现况,乐于聆听各方声音,而他庆幸能与良十四世分享更多不同来源的消息,襄助他充实对中国课题的认识。
周守仁续指,良十四世曾在担任圣奥斯定修道会总会长时前往中国大陆,对中国有一定的认识。
据周守仁转述,良十四世现阶段愿意延续已故教宗方济各对中国的方向,并认同教会与中国政府对话的重要性,同时将在中梵关系上优先透过交谈处理问题。
今年4月逝世的教宗方济各在任内对中国采取务实态度,希望通过对话化解中国教会的复杂处境。他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但未能成行。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9-02 21:18:16 发表 |
| 听说温州农村有个信邪教的,在日历的2012年上画一个圈,然后写上世界末日,结果2012年世界末日没来,他的末日来了,出门让车给轧死了。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8-11 06:48:10 发表 |
| 小德兰书屋的恐吓:16亿人死于“末日天罚”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8-11 04:07:27 发表 |
| 天主教内部的觉醒和瓦解比我预计得更严重,韩清平这篇41点赞,64转发。革天主教的命。哈哈哈哈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8-11 03:55:54 发表 |
| 天主教内部的觉醒和瓦解比我预计得更严重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8-11 00:44:06 发表 |
| 圣经:充满偏激的垃圾自嗨文学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8-10 15:02:01 发表 |
今天细读上述德里奥修女的两篇博文,不难体会到她一直以来的担忧和希望: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宗教,如果依然延续着自第四-第五世纪经包括君士坦丁(Constantine)和戴奥陶西一世(Theodosius I)皇帝分别予以“合法化”(313 AD)和“国教化”(392 AD),又被希腊哲学“浓妆艳抹”后的模样,遵循着将神和世界、物质和精神、身体和灵魂、人与自然分离对立的“二元论”(dualism)思维,并将人的堕落和神的救赎当成构建整个系统神学的“蓝图”,则不但自身的“危机”和“不舒服”不可能消失,而且会无助于她希望带给“救恩”的整个世界,甚至,还有可能加剧已经存在的问题
——
天主教的信理都是从圣经提炼出来的,现在全盘推翻。可是作为神父,韩清平不敢直接否定圣经。哈哈哈哈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8-10 08:35:17 发表 |
| 西方人研究神学研究了两千多年,最后回去研究中国道德经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8-10 05:20:24 发表 |
看了德里奥修女的两篇最新博文,我也有感而发了
韩清平 2025年08月09日
本公众号此前曾多次要么撰文介绍,要么翻译刊发其博文的伊利亚·德里奥(Ilia Delio)修女——这位当今将德日进神父的先知性思想和AI时代的社会和宗教问题,用基督信仰的视角来加以整合、剖析和展望的神学家暨家——在其创建的“基督生成中心”网站上发表的两篇最新博文分别是《基督宗教在危机还是在转型中?》、《为什么基督宗教不舒服》。
虽然我曾在此公号要么自己撰文,要么通过其他人翻译其博文,多次介绍过德立奥修女的思想,但迄今为止,我认为最全面和最有系统的介绍依然是我写的这篇书评“天主”不是“sky god”,“上帝”不是“emperor above”:读德里奥修女新作后的感和评,供有兴趣和耐心的朋友们一读为快!
今天细读上述德里奥修女的两篇博文,不难体会到她一直以来的担忧和希望: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宗教,如果依然延续着自第四-第五世纪经包括君士坦丁(Constantine)和戴奥陶西一世(Theodosius I)皇帝分别予以“合法化”(313 AD)和“国教化”(392 AD),又被希腊哲学“浓妆艳抹”后的模样,遵循着将神和世界、物质和精神、身体和灵魂、人与自然分离对立的“二元论”(dualism)思维,并将人的堕落和神的救赎当成构建整个系统神学的“蓝图”,则不但自身的“危机”和“不舒服”不可能消失,而且会无助于她希望带给“救恩”的整个世界,甚至,还有可能加剧已经存在的问题,如生态恶化、以神和正义的名义宣扬并扩散仇恨和暴力、将宗教信仰功利化、商业化——别说这是基督宗教在历史上和当下的特例,且放下以神和正义的名义来滥杀无辜的恐怖分子和反恐政府不提,看看最近举世闻名的少林寺前方丈过山车般的宗教和人生轨迹,我们就不难明白宗教信仰被扭曲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看过德里奥修女的两篇最新博文后,我在其中一篇下面这样留言说:倘若基督宗教能更深入地理解和欣赏东方灵性传统——如不二论吠檀多(Advaita Vedanta,公元8世纪兴起)、禅宗(Zen Buddhism,公元6世纪兴起)、道家(Taoism,公元前6世纪兴起)等——而非仅仅借鉴希腊哲学,它的历史与现状或许会截然不同。又或者,若基督宗教能以更多谦卑和开放的态度倾听诺里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1342–1416)、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约1260–1328)、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1918–2010)等自家神秘主义者的声音,当今世界与教会面临的许多危机,本可能以更深刻的智慧和更圆满的方式化解。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若基督宗教未曾忽视被荷兰的犹太教视为异端而开除了教籍的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德国哲学家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1775–1854)、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等哲学领域内的“哥白尼式的思想家”们的深刻洞见,也没有忽视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玻姆(David Bohm,1917–1992)等科学先驱的“颠覆性”认知,教会体制与所谓世俗世界之间的鸿沟,今日或许也不会如此之深。
是的,这些感叹都是我在“如果……”的前提下发出的,但历史并非按照包括我在内的某些人的假设发生的,而是就如此那般地发生了。然而,即便如此,从如上我感叹语中提及的,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来交叉比较、分析的各宗及各域大师的名称和年代看,一个不容置疑的实施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无论是某些人还是整个人类希望保持“原地踏步”甚至“回归旧时代”,柏格森所提出的、也是深远地影响了德日进对“进化”予以全新理解的“生命冲力”(élan vital)这一具有革命性的概念——进化中的一种生命的推动力,它不是随机或机械的,而是自发的、充满可能性的——所揭示的那样,一切都在“意识流”的“绵延”(La durée) 中创造着新的可能,而推动和引领这一在“绵延”中不断“创新”的“生命冲力”,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当然会用“神”、“天主”、“上帝”来命名。其他宗教信徒自然有他们喜欢的名称,但,无论选择什么语言、什么符号的名称,只要喻指的就是élan vital,则我们可以欣慰地说“条条大路通绝对精神(黑格尔语),也通奥迈加点(德日进语)”!
最后补充一句:我看到黑格尔的同窗好友,少年天才谢林曾这样说:“自然是可见的精神;精神是不可见的自然。”这让我立即想起德日进的这两句名言:”物质是运动的速度慢到可以被看见的精神”;“我们不是有灵性经验的人,而是有人性经验的灵。”——这本身就是“绵延”和“创新”!
——
看到没有?道家(Taoism,公元前6世纪兴起),天主教怎么这么迟钝,现在才领悟。哈哈哈哈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8-07 01:33:37 发表 |
第二, 由于其全知、全能, “上帝对整个宇宙就只有一道命令, 用这道命令他就决定了允许整个宇宙由可能性而进入现实性”[3] (第77页) 。上帝无限的理智使其在创世时一次性地赋予了世界以尽可能完善的理性的秩序。上帝创世之后只需维系事物的存在, 而不用干涉事物的进程, 因为上帝赋予了事物以它们所可能具有的最高的完善性, 使它们可以按照上帝所规定的秩序自发运行。
——
在实践中就是这样。祈祷改变不了什么。哈哈哈哈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8-07 00:44:32 发表 |
莱布尼茨生前致力于构建一个人人可以理解的“上帝”,请看下文:
桑靖宇:莱布尼茨的神学理性主义及其对中国理学思想的解读
摘要:莱布尼茨继承了中世纪的神学理性主义思想, 并加以彻底理性化, 使上帝成为理性秩序的化身, 从而无需干涉世界。正是这种独特的神学思想使莱布尼茨在中国理学思想中找到了强烈的共鸣, 即理性主义的天道观和有机的自然论。莱布尼茨关于中西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构想, 在今天仍有着现实意义。关键词:神学理性主义; 上帝; 单子; 理; 气; 本文原载《“哲学:基础理论与当代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作者桑靖宇,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17世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们关于中国文化是否与基督教相通融的争论传到欧洲本土时, 引起了欧洲文化界对中国思想的极大兴趣, 以至于谈论中国成为了18世纪知识界的一大时尚。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激进的自由思想家还是保守的神学家, 基本上都认为中国儒学类似于斯宾诺莎的无神论, 与基督教是相冲突的, 因而对之或褒或贬。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 (1646-1716) 却认为中国儒学是一种自然神学, 与基督教是相融合的, 主张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可在自然神学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互相交流, 以促进全人类的福祉。他的上述思想集中表现在去世前夕 (1716) 所著的《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一书中。莱布尼茨为何会力排众议, 采取这种宗教融通主义 (religious accommodationism) 的态度呢?要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先从他本人的神学思想说起。
一、莱布尼茨的神学理性主义
17世纪的欧洲处于严重的宗教冲突之中, 天主教和新教的尖锐对立四处蔓延, 1618-1648年的30年战争更是使德国处于一片瓦砾之中。莱布尼茨自青年起就有个坚定的信念, 即只有在天主教与新教的和解及统一的基础上德国才能摆脱割据走向富强, 也只有如此欧洲才能真正实现和平和繁盛, 从而基督教各教派的统一构成了他毕生的努力目标 (无论是政治活动上还是学术思想上) 。他的神学、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试图为基督教的教派统一提供一个基于理性的、各方都能接受的理论基础。莱布尼茨1668年的《天主教证明》 (Catholic Demonstrations) 为我们勾画出了他的力图给欧洲带来和平的宏大计划的大致轮廓。该计划有三个部分及一个导论。第一部分, 关于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的证明, 即自然神学;第二部分, 关于基督教信仰或启示神学的证明;第三部分, 关于普遍教会及圣经权威的证明。莱布尼茨认为, 必须有一个导论来为这些证明奠定基础, 该导论具有某种百科全书式的性质, 包括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等基本原则[1] (第109页) 。1686年的《形而上学论》 (其成熟思想的标志) 即是该导论的一个重要工作。莱布尼茨的具体思想虽然屡经变化, 但他终其一生都未偏离《天主教证明》的基本思路。莱布尼茨的神学思想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 即使是 (由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而) 不能为理性所直接证明的启示神学的信仰, 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圣餐等在他看来也是与理性不冲突的。他认为只有在理性的基础上基督教各教派才能克服分歧, 达成共识, 从而为世界带来永久的秩序。下面我们将论述莱布尼茨自然神学 (即能为理性所直接把握的神学部分) 的主要思想。处于莱布尼茨自然神学核心的是神学理性主义 (theological intellectualism) 的上帝观念, 即上帝的理性是高于意志的, 而对各种神学意志主义 (theological voluntarism) 的批评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莱布尼茨的神学理性主义的上帝观念可简单归结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 上帝作为最完善的存在, 其行为都服从理性的指导。与神学意志主义者极力推崇上帝意志的至高无上性截然不同, 莱布尼茨认为:“任何意志都包含了意欲的理由, 而这理由自然是高于意志的” (《形而上学论》第2条) [2] (第55页) , 即上帝的理智是优先于意志的。为了避免陷入斯宾诺莎式的决定论, 莱布尼茨认为, 在上帝的理智之中存在着无数的可能世界, 上帝的意志根据最佳者原则选择理性所指明的最佳世界, 并使其现实化。这样, 莱布尼茨认为尽管上帝的意志行为是为理性所决定的, 但在逻辑上上帝做其他选择并无矛盾, 因此上帝的意志仍是自由的。第二, 由于其全知、全能, “上帝对整个宇宙就只有一道命令, 用这道命令他就决定了允许整个宇宙由可能性而进入现实性”[3] (第77页) 。上帝无限的理智使其在创世时一次性地赋予了世界以尽可能完善的理性的秩序。上帝创世之后只需维系事物的存在, 而不用干涉事物的进程, 因为上帝赋予了事物以它们所可能具有的最高的完善性, 使它们可以按照上帝所规定的秩序自发运行。第三, 与自然神论者不同的是, 莱布尼茨承认神迹的存在,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上帝作为超世界的理智 (supramundane intelligence) 需要干涉世界。在他看来, “神迹虽然违背了 (人们有限的理智所认识的) 低等的规则, 但却服从于普遍的秩序。……既然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有秩序的, 那么神迹就跟自然事件一样有秩序。” (《形而上学论》第7条) [2] (第58页) 。因此, 莱布尼茨的世界是彻底理性化的, 上帝不是莫测的神秘力量, 而是理性秩序的化身和保证。莱布尼茨的神学理性主义上帝观对他的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种不干涉的上帝导致了他的有机论的世界观, 即世界是能动的, 能够按照 (上帝创世之初赋予) 自身的规律自发地运作。由此出发, 莱布尼茨批判了近代占主导地位的机械论的、僵死的物质观, 认为无论是笛卡儿派的广延还是伽桑狄、牛顿学派的不可分的原子均不能说明物质世界的有规律的守恒运动, 物质的本质必须是某种能动的力。在其晚期思想中莱布尼茨把这种能动的力归结为精神性的单子, 认为只有单子才是自足的个体实体, 而符合机械论原则的物质只是彩虹般的现象。由于单子是彻底自足的, 不受外界的任何作用和影响, 从而单子之间以及单子与物质现象之间的关系就不是现实的相互作用, 而是上帝创世之初所预定的“前定和谐”。莱布尼茨的神学理性主义精神还鲜明地表现在他对“上帝之城”的普遍化的理解上。上帝之城本是奥古思丁提出的宗教政治学概念, 是指与世俗城邦截然不同的基督教会。但莱布尼茨突破了这种宗教上的狭隘性, 认为所有人类的全体构成了上帝之城。莱布尼茨极大地淡化了基督教的原罪说, 认为人作为上帝的肖像被赋予了理性能力, “能够认识宇宙的秩序, 并在一定程度上能通过例如建筑来模仿它, 每一心灵在自身领域内就像是个小神” (《单子论》第83条) [2] (第280页) , 从而都是上帝之城的成员。当然, 莱布尼茨的这种思想并非是要彻底取消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区别, 而是指每个人都可以凭借理性的正确使用而认识到上帝的存在, 而信仰只是完善人的这种自然神学的理性认识而已。总的来说, 莱布尼茨虽然终身都坚持路德教徒的身份, 但其神学思想更接近于以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的神学理性主义传统, 是对经院哲学与近代哲学加以综合的理性化的创造性尝试。这使得他在反经院哲学蔚为潮流、神学意志主义普遍流行的早期近代显得颇为异类, 他的教会再统一的宏大规划最终只能流于空想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莱布尼茨对中国思想 (理学) 的解读
莱布尼茨的《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是对龙华民、利安当等人的中国思想是无神论的反通融主义 (anti-accommodationism) 的一个批判性的回应。值得注意的是, 莱布尼茨在该书中所提到的中国思想资料基本上转引自龙华民、利安当的相关著作, 也沿袭了他们的错误, 如把“理”、“太极”等理学思想误认为是属于先秦儒学的。限于篇幅, 本文将重点讨论莱布尼茨是如何以其神学理性主义来解读理学思想的。龙华民、利安当等人认为中国思想中缺乏作为人格神的上帝, “理”、“太极”虽貌似基督教的上帝, 但实质上只是原始物质 (prime matter) 而已, 中国人根本就没有精神实体的概念。但莱布尼茨却从他们关于中国思想的引文中看到了类似于他的上帝观念的东西。莱布尼茨对把“理”视为是原始物质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根据[中国人], ‘理’或‘太极’即是至善的‘太一’, 毫无任何杂物的纯善, 既纯又善的本体, 造成天地的本源, 至高的真理。‘理’本身既是力而不限于本身;又为了与众沟通而造了万物, 它是纯、德与爱之源。它的原理即是造万物, 而众善都出乎它的要素与本性。……我们可以假定‘理’、‘太极’或‘上帝’是有灵性的, 能洞窥一切、知道一切, 做一切的。那么, 中国人不可能同时说这么多好, 并且又相信它无用处, 无生命, 无意识, 无灵性, 无智慧, 而不现出矛盾”[4] (第79页) 。即“理”作为创造、主宰万物的能动性的纯善与经院哲学的纯被动性的原始物质恰恰是截然相反的, 倒是类似于基督教的“上帝”。莱布尼茨进而指出:“若是中国古典作者否认‘理’或第一本原有生命, 知识, 力量, 他们指的, 无疑是有人形的、存在于受造物身上的[生命、知识、力量]。他们指的生命, 是感官的活力、知识, 是理性或体验带来的知识、力量, 使王子或官吏通过威严和希望而管辖庶民时的势力。”[4] (第83页) 按照他的解释, 中国人之所以否认“理”具有生命或力量, 是反对将最高实在拟人化, 这一思想与伪狄奥尼索斯的“否定神学”是一致的, 这并不表示“理”不是能动的精神实体。反通融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 “理”产生万物, 并不出于意志或计划, 而是表现为自然律, 万物依照这自然规律而产生、运动, 无需外在的干预。例如培尔 (Bayle) 和马勒布朗士等深受笛卡儿哲学影响的神学意志主义者 (theological voluntarianist) 认为, 如果自然规律是由神的理性所规定的, 那么自然就有了某种独立性, 神的万能也就受到损害。从而, 他们认为, 自然界并没有自在的规律, 一切都处于神的意志的掌握之中。也正因此, 崇尚客观秩序的中国理学思想被培尔、马勒布朗士、龙华民等神学意志主义者视为是斯宾诺莎主义、即无神论的典型。如前所说, 莱布尼茨的神学理性主义是与神学意志主义正相对立的, 他认为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神学意志主义只会造成宗教与科学间的对立以及加剧教派之间的冲突。他很自然地把“理”通过自然规律产生万物的理学思想引为同道, 认为“理”正是他所理解的不干涉的、理性的上帝。如前所说, 莱布尼茨是用“可能世界”的理论来调和神的万能与客观的自然规律、神的意志与其理智之间的张力, 同样, 他也用这种“可能世界”的学说来解释理学思想:“我相信我们不用违背中国人古代的学说, 即可说‘理’凭着本身的完美而从多种可能性中选择最妥善的一种, 因而产生‘气’或物质, 但[气]因备有其本能, 而使其他的[万物]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中国人非但不应受责备, 而且他们的事物因自然本性和预定规范而产生的这项理念, 实在值得受人称扬。”[4] ( 第86页)理学思想中引起莱布尼茨强烈共鸣的不仅仅是通过理性秩序来统御世界的“理”, 还有世界的有机性。实际上, 早在与来华传教士白晋的通信中 (1697-1698年) , 白晋就指出莱布尼茨的物质本质是力的有机论哲学与中国思想有着显著的类似。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中, 莱布尼茨则直接用他的单子—物质模式来解释理学的理气关系。在该书第14条莱布尼茨说道:“这位作者[ 朱熹]很聪明地指出, 鬼神不仅仅是气, 而是气之力。如果孔子对他的一个学生说鬼神仅仅是气, 他指的是有活力的气, 并且是因为这位学生的理智能力不能理解精神实体, 才因此而因材施教。对希腊人、拉丁人来说, Pneuma和Spiritus意味着空气, 那是一种微妙的、有穿透力的物质, 被创造的精神实体实则被其所覆盖。同一作者 (指朱熹) 还提到鬼神即理。”[5] (第87页)莱布尼茨尽管对理学思想存在着误解——如将理与鬼神等同起来, 并将它们都视为是精神实体, 但难能可贵的是, 他不但反对龙华民、利安当将理视为是惰性的原始物质的谬误, 还进一步觉察到气也非僵死的原始物质, 而是“微妙的、有穿透力的”、生机勃勃的东西, 类似古代西方人所说的空气。莱布尼茨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理解显然与其自身的有机论哲学观密不可分。在他看来, 物质的本质既非是广延, 也非是不可分的原子, 而是能动的力, 物质的力源于与其结合在一起的能动的精神实体——单子。莱布尼茨认为朱熹的理是类似单子的能动的精神实体, 它赋予了气以活力和生机。“ (朱熹还认为) , 事物除了精粗, 厚薄之外, 并无其他差别。他想说的, 显然并非理或鬼神是物质性的, 而是这些物质为鬼神所赋予生机, 那些与不那么粗糙、不那么厚重的物质结合在一起的 (理或精神实体) 就更为完善了。……个别的理是那伟大的理的 (比照着他们躯体的) 不同完美程度的散射 (emanation) 。因而事物的不同与他们物质的微妙性与粗重程度成比例, 因为理本身与它们 (指理所依附的物质) 相对应。”[5] (第88页) 莱布尼茨从朱熹的理气不离以及事物因气的清浊、厚薄不同而不同中再次看到了他自己的哲学。莱氏认为, 除了作为最高单子的上帝之外, 任何被创造的单子都因不同程度的模糊的知觉而与相应的物质躯体相伴随, 越高级的单子的物质躯体越精细。正是这种心物不离的有机论哲学观使得莱布尼茨得以克服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论及其僵死的物质观, 使得物质得以分享了精神的活力和生机。莱布尼茨的这种有机论哲学思想受到科学史家李约瑟的大力赞赏。李约瑟将莱布尼茨视为是现代西方有机论思想的直接先驱, 并猜测他的有机论哲学可能是受到中国思想的启发:“当它 (有机论思想) 来临的时候, 人们发现一系列的思想家已经为它准备了道路——从怀特海回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 又从黑格尔回溯到莱布尼茨——然后大概灵感就不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受益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地方, 比这世界已经意识到的要更多。”[6] (第505页) 李约瑟的这一设想固然令人振奋, 但正如本文所分析的, 莱布尼茨的有机论哲学是有其自身的思想根源的, 即对上帝进行充分理性化的结果——上帝对世界的不干涉使得世界按照自身的规律和动力运作。有意思的是, 中国的有机论思想某种意义上也是这种宗教转换的结果——即对上古的人格神加以理性化, 这一过程在理学思想中达到顶峰。值得一提的是, 莱布尼茨对中国的态度与他的理性主义的“上帝之城”的思想也颇有关系。在他看来, 既然中国思想通过理性认识到了上帝的存在, 那么中国人就现实地是上帝之城的成员, 从而他的基督教会统一计划就进一步扩大到把中国也包括进来。他热情地指出:“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 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中国。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决定。也许天意注定如此安排, 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 也会把它们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7] (第1页) 莱布尼茨尤其对中国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哲学推崇备至, 他说道:“鉴于我们目前面对的空前的道德没落状况, 似乎有必要请中国的传教士到欧洲给我们传授如何应用和实践自然神学, 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向他们传授启示神学一样。”[7] (第6页)
三、结 语
以上从莱布尼茨的相关著作出发, 扼要地论述了他的神学理性主义及其对中国 (理学) 思想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 在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 即理性主义的天道观和有机的自然观。实际上, 尽管在莱布尼茨哲学与朱熹理学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差异, 但两者之间的类似性比他所知道的多得多:如在认识论上, 莱布尼茨既认为一切观念都是天赋的, 又主张经验的“助缘”对于认识天赋观念的重要性, 这与朱熹的“心具众理”、“格物致知”的思想若合符节;在伦理学上, 他们都很推崇理性认识对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在政治哲学上, 他们都强调德性的首要地位, 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在今天看来, 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阐释有着明显的不足, 如资料的局限性, 较浓厚地将中国思想套入西方框架的西方中心论的痕迹。但莱布尼茨的深刻之处在于, 他坚信人类有着共同的天性和基于自然的理性, 因而文化间在差异的表象之下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他用自己卓越的才智在当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创造性地揭示了中西文化间的契合。正如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艾田蒲所说:“在1700年前后, 关注中国的人之中, 莱布尼茨无疑是最了解实情、最公平合理的一个, 他的著作也是唯一一部我们今天还可以阅读的著作。”[8] (第385页)反观当代的文化比较, 人们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 似乎更注重文化间的差异性, 但莱布尼茨注重寻找文化间共识的努力是值得人们重视的。对莱布尼茨而言, 这种文化间的契合绝不仅仅是空洞的思想而已, 他穷其一生的努力都是在政治、外交、文化等多方面社会活动中, 试图缔造一个基于人类共同的理性 (即自然神学) 的人类共同体, 将破碎的欧洲整合起来, 并进而使欧洲和中国能够紧密联合, 取长补短, 通过发扬人的理性和科学精神, 消除世界上的各种混乱和纷争, 建立一个极大地促进人类福祉的新世界。莱布尼茨的宏伟构想固然失败了, 他的普遍理性主义思想也不免忽视了文化间的差异, 但是一个有希望的人类未来除了建立在文化间的共识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如果我们不愿赞同亨廷顿的文明间必然冲突的理论的话, 那么莱布尼茨关于东西方文化大融合的宏伟构想就仍不失为我们努力的方向。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8-07 00:43:09 发表 |
是时候让基督信仰升级为“宇宙版”了
韩清平 2021年02月11日 10:43
昨天,看了刊于科普电子杂志《返朴》上由刘全慧博士撰写的《杨振宁和爱因斯坦不断提到的宗教体验是什么?》一文,感到眼前一亮。我觉得他通过杨、爱二位科学巨匠的个人体验和见证,所要表达的正是本人这些年来在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神父、洛尔(Richard Rohr)神父、德里奥(Ilia Delio)修女等公教思想家的引导启发下,努力去追求和传播的理念:基督信仰必须要跳出建立在“地心说”和“二元论”基础上的法律化和哲学化的思维模式,由“为恭敬天主,救自己的灵魂”转向像圣保禄宗徒所希望的那样,去“领悟基督的爱是怎样的广、阔、高、深,并知道基督的爱是远超人所能知的”(厄弗所书3:18-19)。
在其文章中,刘博士特别介绍了早在1930年,爱因斯坦在写给《纽约时代杂志》的文章“科学与宗教”中,对“宇宙宗教体验”(cosmic religious sense)和“宇宙宗教经验”(cosmic religious experience)的定义和系统的论述。简言之,爱氏认为,凡是对宇宙的和谐与自然法则有认知的人,特别是科学家,就不可能不由衷地产生与历代宗教大师们非常相似的宗教感情。他们在表达方式上可以不同,但“对存在之中显示出来的合理性至为崇敬和感动……从而对存在之中的庄严理性心生谦卑”。在爱氏看来,这种态度正是最高意义上的宗教态度。
无独有偶,过去这些天来,我花了不少时间来了解美国著名宇宙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生前的一些著作和演讲。他的科学遗产及影响力实在无法用三言两语说清楚,但他制作的“宇宙年历”,以及对着“旅行者一号”在1990年,从距离地球64亿公里外的太空拍摄到的图片——一个小小的淡蓝色圆点——写下的《暗淡蓝点》(Pale Blue Dot)一书,令我惊叹称奇的同时,也产生强烈的共鸣。按照萨根的“宇宙年历”,如果把宇宙138亿年的历史压缩为人类的1年,人类时间的每1秒相当于其450年、1小时相当于166万年、1天相当于4000万年,一个人活到80岁,宇宙才过去了0.18秒。
看着这“宇宙年历”,听着萨根对“暗淡蓝点”的感慨(见下图),我不由地再次陷入了沉思:人类的出现和存在是必然还是偶然?再过1万年,也就是宇宙时间再过22秒后,生活在耶稣诞生(处于宇宙年历的12月31日晚11点59分56秒)后的2021年,饱受新冠肺炎疫情困扰的人类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会像6500万年前的恐龙一样彻底消失吗?如果能活下去,会对宇宙奥秘、对神灵的认知上升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和宇宙中比我们的智慧度更高的生命相遇呢(就像不久前看过的《星星的孩子》系列著作所描写的那样)?
是的,我知道有人会笑我异想天开,或者“杞人忧天”,但我却认为这样的想法或“忧虑”,虽然听上去太遥不可及,正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具体表现。正如卡尔·萨根的这句名言那样:“宇宙就在我们内,我们是由星尘构成的,我们是宇宙了解其自身的一种途径”。
而有同样想法的是比他早了半个世纪的德日进神父:“我们不只是把思想看作是参与进化过程的一种异常现象或副现象,而也要把进化看作是可简化和可识别为朝向思想的一种进展,也就是我们灵魂的运动是在表达和测量进化本身的进展阶段。人类终于发现,他只是进化变得意识到了自己而已。”
正是基于这样的意识和理念,在其代表作《人的现象》一书中,德日进在讲述了宇宙从“生命之前”到“生命”到“思想的出现”后,也展望了“超人格”的未来。也就是说,宇宙的进化绝不会因为有了像我们这样的人类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是还会继续朝着奥迈加点(Omega-Ω-Point)不断地向前向上,直至“宇宙基督”(Cosmic Christ)的奥秘完全彰显出来……
鉴于此,当代德日进思想专家,美国方济各会修女德里奥,在德日进思想及其弟子马绍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对通讯媒介的认知(*他常说“媒介即讯息”,意思是媒介所传播的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这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以及它所开创的可能性及带来的社会变革。)基础上,完成了新书《让地球再次着迷:为什么人工智能也需要宗教?》。德里奥在对自己的新书简介中这样写道:
书中汲取了耶稣会科学家德日进的深刻见解,追溯了人类意识在科技发展过程中的崛起,指出电脑和人工智能(AI)通过电子连接手段,促进了人类意识复杂化,从而最终扩展了人类意识……德日进将人、神和科技导致的进化结合在一起谈论,指出宇宙意识层面上的新型人类正在诞生。在他看来,这种进化带来了对神的新理解。他看到,由于科技扩展了人类意识,因此,神与世界的关系正在通过科技走向更广阔的合一。书中还探讨了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哲学轨迹,强调人的提升,并探讨了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强调深层关系,以及对科技进化过程中崛起的新型人类的认可和选择,即“超人”或“后人类”。他们与现代人类相比,具有不同的逻辑结构、不同的意识轴心。(*译注:超人类主义认为,通过科学技术,人类可以克服生理和智力上进化的局限性,超越目前意义上的人类。后人类主义认为,人类以现代高新科技为基础,将纯粹的自然人进行设计、改造、升级后,产生的一方面或几方面超越普通人类的“新型人类”,这些“人”不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而被称为“后人类”。)简而言之,对神学和大多数学科来说,人工智能邀请我们反省思考我们正在创造怎样的世界。它就像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我们将会看到我们自己、看到我们正在变成什么样。科技正在影响着人类人格的深度,也在影响着宗教的深度。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考虑发展适应科技时代的神学理论,这样,人类才不会陷于“科技将实现宗教承诺”的诱惑。
上述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经验”、萨根的“宇宙年历”和著作、德日进的“宇宙基督”论、德里奥的新作,似乎是零散的思想火花,但其实是促进基督信仰升级为“宇宙版”的共同推力。他们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宇宙进化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表面上是对传统宗教信仰的淡漠和冷却,但事实上是在追求着对神和灵性生命的更深和更进一步的认识——就像电脑和手机需要升级,宗教亦然!因此,摆在包括基督宗教在内的各大宗教面前的挑战和任务,不是人们和宗教信仰决裂后该何去何从,而是如何让我们所信从和宣讲的天主/上帝/神更能让当今和未来时代的人们心服口服地接受。而这正就是近一个世纪前的德日进努力表达的:“我们正在开始明白,而且将永不会忘记,将来唯一对人有可能的宗教就是在一开始便教导他满怀激情地去认识、关爱并服务他也是其中一员的这个宇宙。”走笔至此,我突然意识到,虽然仍然没法确切回答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但却感到当下这一刻活得更加有意义、有希望、有喜乐了:在如此浩瀚的宇宙空间和如此漫长的宇宙年历中,我竟然有机会作为其中一员而参与其中,并且有能力体验、观照、反思——你我他/她,何德何能?如此地微不足道,但又如此地不可或缺;如此地转瞬即逝,但又如此地亘古永恒;如此地形单影只,但又如此地浑然一体……此无它,只因为我们都是“自起初就有的天主圣言/道”,通过不断的“成为血肉”而出现、存在、参与的表现,如今正在继续书写着又一个新年来临之际的“宇宙年历”!谨以此拙文,恭祝各位读者朋友新年快乐、健康平安,并谢谢你们的批评指正、鼓励支持!!!
——
批注:德日进更多的是一位科学家,所以从科学的角度理解上帝,所以最终和爱因斯坦一样。而爱因斯坦说:我信的是斯宾诺莎的上帝。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8-06 23:13:28 发表 |
| 他化自在天的天主就是魔!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8-05 06:21:18 发表 |
神学辞典:自然神论
(一)概念说明:自然神论deism此词来自拉丁文Deus (神)。在十九世纪以前,deism与theism (有神论,来自希腊文Theos)是同义词。从第十九世纪以来,「自然神论」被用来指称许多不同的神哲学思想;它们虽然不否认神的存在,却都拒绝接受传统基督徒对神和宇宙的关系的看法。
(二)自然神论有许多种不同的模式:
(1) 与传统思想最接近的一种,不但同意天主创造宇宙,也承认宇宙万物(包括人类)都接受天主的安排眷顾,甚至相信死后的赏善罚恶。它所拒绝的是天主的启示;强调人必须依靠自己的理性才能认识天主的存在和本质,才能认识人的伦理责任。
(2) 另一派自然神论却否认来生,人类的功过赏罚尽在此生。
(3) 比较极端的自然神论则认为天主的安排眷顾只表现在大自然,而不及于人的道德行为上。人类在今生所尝到的苦与乐都与天主无关,美德就是自己的赏报。
(4) 最极端的一种只承认世界的创造源自一位智慧大能的神;祂在已存在的物质中加上秩序,依据祂所规划的自然律,宇宙得以运作。但是这位大能的神绝不干预既定的宇宙秩序;准此,自然的运作绝无例外的事。换言之,奇迹是不可能的。再者,天主对个别的人和事也不闻不问。然而,人类的幸福却在乎他能否认识且喜爱这位造物主,及能否公正无私地与同侪共处。
(三)自然神论产生的因素很多。十七世纪,基督新教对教会传统的圣经解释法提出质疑,此举却暴露了圣经中许多似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看来,它只是一本古代文学作品的总集,与许多同类型的作品一样烙印着科学的谬误与文化的独特性。批判的心灵既无法接受此乃天主的启示,人只能自求多福,依靠自己的理性和经验来认识天主了。
然而导致自然神论的产生,最有力的因素也许还是新科学的兴趣。十六、七世纪科学上的新发现改变了欧洲人对宇宙的基本看法。在加利略(G. Galilei, 1564-1642)、牛顿(I. Newton, 1643-1727)等人的影响下,老式的基督徒化的亚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宇宙观不得不让步了。亚里斯多德曾假定在一位「第一不动的动因」(first unmoved mover)的推动下,天体绕着地球作圆周性的运行,这种思想已经由于地球吸引力、万有引力、及惯性等等的发现显得过时了。反之,世界就好像一部完美的机器一样,无须任何修整与调适,它的操作完全按照物理的定律运行。这一切都鼓励自然神论的产生,天主与世界的关系只好像是一位元始的工匠与祂的制成品的关系一般而已。
非基督宗教文化的影响对自然神论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关系。十六七世纪航海事业的发达扩大了欧洲人的视野,他们目睹许多非基督宗教的文化与它们高度的伦理系统及宗教原则。这些耳闻目睹的经验在在显示出人类智慧的辉煌成就。看来,要建立宗教和伦理的原则,人类的理性已经足够了。换言之,天主的启示和神律都变成了多余的名词。
——
一般的信徒有空应该多读书,多涉猎,不要以为一本圣经就是一切。你们的神父的思想都已经转变了,而且我知道有不少神父都是这么想。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8-05 06:12:06 发表 |
再回顾他之前的文章:
今天,面对依然肆虐的洛杉矶“火魔”,我继续反省“神的无能”
原创 韩清平 清平思域 2025年01月13日 00:02 河北
在昨天的小文《洛杉矶“火魔”依然肆虐中,教宗方济各致电当地总主教》中,我除了报道教宗方济各向正在被“史无前例”的火灾肆虐的洛杉矶的总主教拍发电文,表达慰问和祈祷,也简短地阐述了自己的一些感想和心情。
就在今天中午,借主受洗节的三钟经讲话,教宗方济各再次表达了他对洛杉矶人民的关注和祈祷:“我和最近几天正在遭遇致命火灾的加州洛杉矶县的居民们在一起。我为你们所有人献上祈祷!”
教宗昨天拍发慰问和祈祷的电报,今天再次公开表达关切和祈祷,足见这火灾非同小可。从大前天到今天,我脑海中也一直被网络上看到的“末世景象”所充斥,自然也在不断地就此事件和现象进行着或被动或主动的神学和灵修反省。
有不少读者朋友,包括老熟人和新朋友,都被我昨天小文中貌似奇葩但“又很有道理”的“神明观”触动了心弦。远隔千山万水的只能要么文下留言、要么发微信交流,近在身边的干脆直接约我面谈,希望能进一步地探讨神究竟是“也有无能的时候”还是“全能全知”的问题。鉴于此,我希望在此小文中追述一些反省和想法。
首先要说的是,每次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小灾难,有思考能力且容易和神明联系到一起的人,都会有诸如我昨天小文中提及的那些想法和纠结:如果有神,而且是全能全知的,那要么灾难就是祂降下来惩罚罪人的,要么祂就是还不愿意出手相助。因此,人需要继续“烧香磕头献祭悔罪求饶”,直到祂息怒或动容后改变想法——这基本就是大部分传统宗教信仰的教导和逻辑。
与此同时,当有人,如下这本书的作者,提出说“神是软弱的”这一与众不同的想法和看法时,自然会引来一系列的惊叹、谴责和痛骂声。
而这样的遭遇,另一位比昨天提到的伏尔泰更早的启蒙主义思想家、身为犹太人的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年11月24日—1677年2月21日)就已经遭遇了:就因为他认为神和自然是一体,也就是Deus sive Natura这句名言的意思。更进一步讲,斯宾诺莎认为,既然神就是自然本身,神的行为就是自然规律的表现,因此不存在神通过“超自然”或“奇迹”来干预自然规律的问题。
——
理解了吧,韩清平的思想已经从天主教转变为“自然神论”
我还特意加了批注:道德经的观点: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所以,祈祷没用。西方理性三哲莱布尼茨笛卡尔斯宾诺莎领悟这一点比道德经晚了两千年。而天主教神职人员到今天才勉强承认。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8-04 10:42:59 发表 |
| 这叫“自然神论”,是哲学家科学家的信仰。他们的上帝表现为万事万物的规律。因此不存在喜怒哀乐,不会介入人类的命运。牛顿,爱因斯坦,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笛卡尔,他们信的上帝就是这个。也就是道家的“道”,表现为万事万物的规律。没想到啊没想到,韩神父也信了这个,哈哈哈哈。 |
| |
|
| 本站网友 匿名 |
2025-08-04 04:43:52 发表 |
邢文之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以为他是无敌的。哈哈哈,如今一笑而过。
还是来说韩清平吧,他又吹德日进。德日进德核心观点“宇宙基督”,这个宇宙就是基督。一般的信徒听的云里雾里。幸好我了解斯宾诺莎,斯宾诺莎的观点“宇宙即神”。宇宙基督和宇宙即神是一个意思,都是说这个宇宙就是神,神就是这个宇宙。唉,没想到韩清平中毒这么深,而他的粉丝又那么多。天主教徒被所谓的神学家耍得团团转。哈哈哈 |
| |
|
网友评论仅供网友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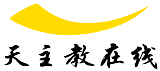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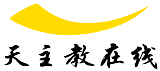
天主教这些反华媒体以前说方济各“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现在是不是继续说良十四“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呵呵!宗教媒体甘做美国的政治工具,你们算老几?